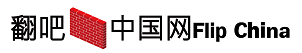None
【2024年04月25日訊】(英文資深記者Jan Jekielek採訪報導)
托比‧羅傑斯:實行了250年的經濟、政治自由主義,眨眼之間就消失了。
楊傑凱:托比‧羅傑斯(Toby Rogers)博士是醫療自由的倡導者、布朗斯通研究所(Brownstone Institute)研究員,研究領域涉及公共衛生、監管機構被綁架、大製藥公司腐敗,以及當今兒童面臨的慢性病流行。
托比‧羅傑斯:太荒唐了,科學垃圾級的東西竟被食品藥物管理局(FDA)、疾控中心(CDC)奉為真正的科學。
楊傑凱:兩年來他評估了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、疾控中心每一次專家諮詢委員會就COVID-19(新冠病毒,中共病毒)疫苗的審批會,他的發現令人震驚。
托比‧羅傑斯:疫苗審批會的統計數據非常荒謬,這些數據連高中生物課都通不過,大學統計學的入門課也通不過。
楊傑凱:這裡是《美國思想領袖》,我是楊傑凱(Jan Jekielek)。
從「左派中的左派」都成為布朗斯通研究所研究員
楊傑凱:托比‧羅傑斯,很高興你作客《美國思想領袖》節目。
羅傑斯:謝謝你的邀請。我是你們的超級粉絲,你們做的訪談節目非常棒。能夠上你們的節目我深感榮幸。
楊傑凱:哇!你讓我一下子不知道說什麼好了,謝謝!我剛剛見證了一場你做的非常精彩的演講,你講述了我們社會所發生的事情,我們所看到的深刻的變化。我覺得非常有意思的一點是你的背景,正如你向我描述的,你是「左派中的左派」。請給我們講講,你是誰,來自哪裡,這些有助於了解待會我們要討論的內容。
羅傑斯:我在南加州一個熱愛教育的家庭中長大,在費城斯沃斯莫爾學院(Swarthmore College)獲得政治學學士學位。之後,我為我能找到的所有優秀的左派非營利組織工作。我為農場工人和小企業援助機構工作過,在消滅貧困計劃、環保計劃、有毒廢棄物處置計劃工作過,電動公交、性少數群體等方面也接觸過。
我發現我喜歡學校,學校讓我覺得很輕鬆。所以我去伯克利獲得了碩士學位,伯克利是一個不錯的左派學府。在伯克利時,我發現自己喜歡教學。然後我就去了澳大利亞悉尼的悉尼大學,在那裡獲得了政治經濟學博士學位。悉尼大學的政治經濟學專業頗具傳奇色彩,它將道德哲學、政治學和經濟學融為一體。我認為人們就應該這樣對待政治和經濟話題。你需要把道德、政治和經濟綜合起來作為一個主題來討論。我研究了亞當‧史密斯(Adam Smith)關於奴隸制的觀點,並為此花了約一年時間。
然後情況發生了變化,我步入了一個不同的方向,這引導我走上了現在的道路。如今是布朗斯通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員,並認同秉持自由意志主義理念的人士,反對製藥業及其對美國社會的控制。所以我的人生經歷是相當政治性的。但我發現,自由意志主義理念者能夠理解美國當前的這場道德、政治和經濟危機中正在發生著什麼。布朗斯通研究所的(創始人)傑弗里‧塔克(Jeffrey Tucker),無疑在做著令人驚歎的工作,我很高興現在能與他們合作。
我們是如何從一個系統轉到了現在這個全新的系統
楊傑凱:請描述一下你怎麼理解這場危機。
羅傑斯:好的,過去250年來,我們一直生活在經濟、政治自由主義之中。每個人都喜歡政治自由,是吧。所以什麼選舉啦,言論自由,宗教自由,集會自由,法院,法治,憲法。廣泛的共識是,政治自由主義太美妙了。亞當‧史密斯給我們引入了經濟自由主義,即自由市場,自由貿易以及賺錢的權利,創業的權利等等之類的事情。在這套體制下我們已經生活了250年。
當前奇怪的是,到了2020年3月,這一切都消失了,政治自由主義不見了,言論自由被禁止了,網絡上有了言論審查。宗教自由被禁止了,你不能在教會裡聚會了,你不能在唱詩班唱歌了。集會自由被禁止了。這一切都在2020年初的時候消失了。這是很奇怪的,是吧?實行了250年的經濟自由主義、政治自由主義,到了2020年年初,眨眼之間就消失了。所以我在Substack平台上努力解讀的很多內容、我為布朗斯通研究所所做的工作,就是努力了解到底發生了什麼。
我們是如何從一個系統轉到了現在這個全新的系統,如果讓我來描述的話,就是製藥業控制了晚間新聞上什麼內容,不是你們()的節目,而是CNN、微軟全國廣播公司(MSNBC)等其它主流媒體的內容。製藥業控制了華盛頓特區的監管機構做什麼事。製藥業控制了科學期刊上發表什麼論文。這是對社會徹底的重塑,藉此製藥業、大科技公司和政府勾結在一起,改寫了我們整個社會的經濟規則、政治規則。
兩年來,我觀看了FDA和CDC專家諮詢委員會每次新冠疫苗許可方面的審批會。這些會議令人震驚。他們的會議很長,八小時的會議,但上演的都是政治戲碼。都是那種跟科學沾點邊的、聽起來相似的東西。這些會上的統計數據是荒謬的,它們連高中生物課都通不過,大學統計學的入門課也通不過。彷彿上演的是一場流行病戲碼,但真正的科學卻墮入了深淵,隨著時間的推移,標準變得越來越弱。輝瑞和莫德納最初針對成人的臨床試驗約兩萬兩千人在治療組,兩萬兩千人在安慰劑組。而當開始對兒童作臨床試驗時,只有幾百名兒童受試者,不足以了解那些疫苗是否有危害。然後加強針方面,他們決定完全跳過人體臨床試驗,因此最初的加強針僅在八隻小鼠中做了測試。即將推出的新加強針在更少的小鼠中進行測試。那些人不是在搞什麼科學,而是在與企業和政府進行有利可圖的勾兌。他們沒有做真正的科學,甚至連邊都沒沾。太荒唐了,科學垃圾級的東西卻被FDA和CDC奉為真正的科學。
博士論文研究發現:製藥業已綁架了政府機構、學術界和媒體
楊傑凱:我想提一點。你對以藥物為導向的科學領域並不陌生。這是你最終關注的東西。也許可以跟我介紹一下這方面的背景。
羅傑斯:好的,我在悉尼大學攻讀博士學位課程一年時,我有自己喜歡的課題,也喜歡悉尼的生活,非常棒。我當時女朋友的兒子被診斷出患有自閉症譜系的疾病。我對自閉症有所了解。在我成長的過程中,我媽曾是一名特殊教育老師,所以我對自閉症略知一二,但從未真正深入研究過。
CDC有關於自閉症情況的描述,但後來我去查了他們的資料來源。就像我現在在新冠疫苗中看到的那樣,他們用於論證自己論點的基本來源很薄弱。相關數據不支持他們的論點,很快就站不住腳了。所以一天的研究變成了兩天的研究、三天的研究。
我是政治經濟學學者,所以我對自閉症的花費很好奇,而自閉症的花費簡直是天文數字。這是2015年的事了。目前,美國每年自閉症的花費是2680億美元,預計到2025年,美國將達到每年一萬億美元。你我都知道美國國防預算每年約八千億美元。自閉症的花費預計到2025年將超過美國國防部預算。這是一個龐大的政治經濟學故事。世界上沒有一個政府問一問為什麼會這樣,這是怎麼發生的。
最終我將我的博士論文主題改成了自閉症政治經濟學。在接下來的四年裡,我閱讀了所有有關自閉症的文章,試圖了解自閉症的政治和經濟動態。我發現製藥業已綁架了各個監管機構,CDC、FDA、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,但被他們綁架的遠不止這些。他們還綁架了媒體、主流媒體。他們綁架了整個科學及醫學知識的生產本身。所以醫學院校的教科書是製藥行業製作的。教授們被收買了,方式是通過獲得研究基金和外出演講等等。醫療領域的繼續教育是受製藥業控制的。因此,我們能進行的任何關於自閉症根源的討論,以及從汞、燃煤電廠的各種有毒化學物質到疫苗的成分,泰諾、SSRIs等各種醫療藥品等都是有問題的。現在這方面我們有非常好的數據。所有這方面的對話都是被禁止的。所以,我發現了製藥業的套路。
這是結構性激勵錯位、社會如何偏離正軌的故事
楊傑凱:我們繼續與布朗斯通研究所研究員托比‧羅傑斯交談。
我必須相信大多數醫生進入自己的領域是為了做好事。也許他們為了自己能做得很出色,並不想躋身於剛才你向我描述的那種體系中。怎麼可能那麼多傑出的、看起來很正派的人完全沒有意識到這種情況,竟然說「這是荒謬的、這是陰謀論」呢?我們常聽到這種說法。不管怎麼說,這就是困難,你總要面對,在任何似乎有悖於我們今天所稱的正確觀點、正統觀點的領域莫不如此。
羅傑斯:是的,說得好。許多參與「醫療自主運動」的人都講述了一個惡魔的故事。幕後惡者、邪惡分子的故事,想要傷害他人並幸災樂禍者的故事。我們已經看到了。
楊傑凱:我只想插一句,我們也知道這些東西的存在。
羅傑斯:非常認同。
楊傑凱:有一些人,但不是所有人或很大一部分人。
羅傑斯:我認為這更多的是結構性激勵錯位了。
楊傑凱:嗯。
羅傑斯:如果你是一位兒科醫生,請注意,我相信大多數兒科醫生都是懷著最好的願望進入這一行業的,希望幫助孩子茁壯成長並擁有最健康的生活。但你從醫學院校畢業時身上背著25萬美元以上的債,你經歷了被住院醫師欺負的過程,熬夜值班,被主任醫師訓斥等等,有這事吧?
最後你終於熬出來了,開始自己行醫了,也許你進入一家醫院工作。有人告訴你,如果你60%的患者完全接種了疫苗,你會得到獎金。你就會想,好吧,今年我要拿到獎金了,這能幫助我還清債務呀。而來年,你70%的患者必須完全接種疫苗。然後是80%的患者必須完全接種疫苗。
到這時,這個系統你已經跟著做了一段時間了,好像也沒什麼問題。長期來看,都是一小步一小步走過來的。所以,我在實際觀察FDA和CDC開會時,看他們在做什麼,醫生們是沒有時間做那些的,是吧。所以他們只能相信別人的話。他們說,好吧,如果CDC和FDA同意的話,那很可能就沒問題了。
所以,我認為這裡有一個我們不太理解的心理過程,人們最終接受了,也成了真正的信徒。他們沒有……我認為他們甚至沒有意識到他們正在造成傷害,或者他們推薦的疫苗未經過適當安慰劑的檢測,尚未被證明可以帶來所聲稱的益處。所以我認為這是一個歷時多年的過程。我認為這很微妙。這是一個好人在某些情況下最終幹了壞事的故事。
注意,漢娜‧阿倫特(Hannah Arendt)解讀了這個問題,方法是試圖了解納粹德國經歷了什麼故事。那是一個關於惡魔的故事,對吧?很多納粹惡魔,黨衛軍,是很可怕的。德國社會中很多人都是很可怕的,但她講述了一個關於官僚們的故事。「平庸之惡」以及官僚機構出台各種激勵措施的方式,導致了一開始誰也不願意看到的結果。這是一個社會如何偏離正軌的社會學故事。我認為美國社會已經偏離了正軌。
在歷史上是如何成功監管其它有毒產品的?
楊傑凱:所以即使設想一下、想像一下似乎都令人畏懼。你認為這方面人們應該做些什麼呢?
羅傑斯:第一部分是如何處置大型製藥公司。好比一個八百磅的大猩猩一樣,所以我們從這裡開始。我在做博士論文期間,研究了成功監管其它有毒產品的監管歷史,包括造成傷害的石棉、菸草、滴滴涕、各種醫藥產品、沙利度胺。隨著時代的進步出現了監管,即使我們跨越時空,回到監管的初期,政府也並非真的想要資助某些研究,因為那些研究可能會毀掉一個行業並導致一種產品退出市場。
你獲得危險品相關的良好科學知識的途徑是通過法院,通過「毒物侵權」系統。所以基本上,原告律師會查看可以找到的有毒產品的任何數據。他們會計算在毒物侵權案件中勝訴的幾率,然後他們會真正去資助科學研究,以弄清楚該產品究竟有多危險。一百年來這個體系就是這樣運作的。
楊傑凱:這是你最終花了幾週的時間通過閱讀研究文獻發現的。業界沒有這麼做,是嗎?
羅傑斯:是的。
楊傑凱:非常有意思。
羅傑斯:是的。所以你實際上需要法院系統,你需要財力雄厚的原告律師,花費一千萬美元、兩千萬美元等等用於研究,這樣你才有數據來弄清楚有毒產品的危害程度有多高。這就是我們體系運行的方式。製藥業過去是知道這一點的。在上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初,他們在有關疫苗傷害的訴訟中敗訴。
如何才能扭轉局面?讓製藥業有動力去生產更安全的疫苗
所以在1986年,他們促使國會通過了《全國兒童疫苗傷害法案》(National Childhood Vaccine Injury Act),這為他們提供了責任保護。如果你的孩子受到了疫苗傷害,你不能將製藥業告上法庭,原因就是這個1986年法案。這是一個單獨的法院體系,它運作的效果不太好。是政府站在製藥業的立場介入了進來,而不是製藥業自己代表自己的利益講話。
因此,要解決強加給民眾的有毒疫苗的問題,方法就是取消對製藥業的責任保護,把他們拉回到法庭上去。讓我們在法庭上一決勝負。讓我們在法庭上、在一個辯論系統內討論數據問題,而不是在被綁架的CDC和FDA討論數據。但你必須廢除1986年法案。你還必須廢除9‧11事件後2000年代初期的《公共準備和應急準備法》(Public Readiness and Emergency Preparedness Act,PREP Act)等等。如果我們這樣做,製藥業將有動力去生產更安全的疫苗。
目前,唯一的激勵是在疫苗接種計劃中儘可能多地增加疫苗,因為這完全是為了盈利,而且沒有任何風險,因為現在不能把他們告上法庭。這就是我們對待製藥業的方式。但製藥業是一個大的利益壟斷集團,還有九個、十個壟斷集團也是有問題的。
我認為有幾件事我們需要做。我們需要恢復反壟斷,我們需要打破一些寡頭壟斷,真正迫使這些公司相互競爭,從而由市場來決定。我還認為,行政機構已經變得太大了。所以我們不再有民選官員、立法者做出決策。行政機構、官僚機構正在制定一半多的支配我們日常生活的新政策,完全失控了。行政機構必須得到完全的約束。國家的規模必須大幅縮小,權力必須下放。我們需要將健康問題從華盛頓特區分離出去,不僅是將其轉移到各州,而是將其轉移到千家萬戶中去,授權家庭和地方管轄部門做出決定。我們必須縮小聯邦政府的規模,這樣他們就不會被綁架,就不會試圖控制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。
楊傑凱:好的,托比‧羅傑斯,很高興你作客我們的節目。
羅傑斯:謝謝你邀請我。非常享受我們這一次的談話。
楊傑凱:感謝各位觀看本期《美國思想領袖》節目我對托比‧羅傑斯的採訪。我是主持人楊傑凱。
《美國思想領袖》製作組
責任編輯:李琳#